我与《戴复古考论》的三十年研究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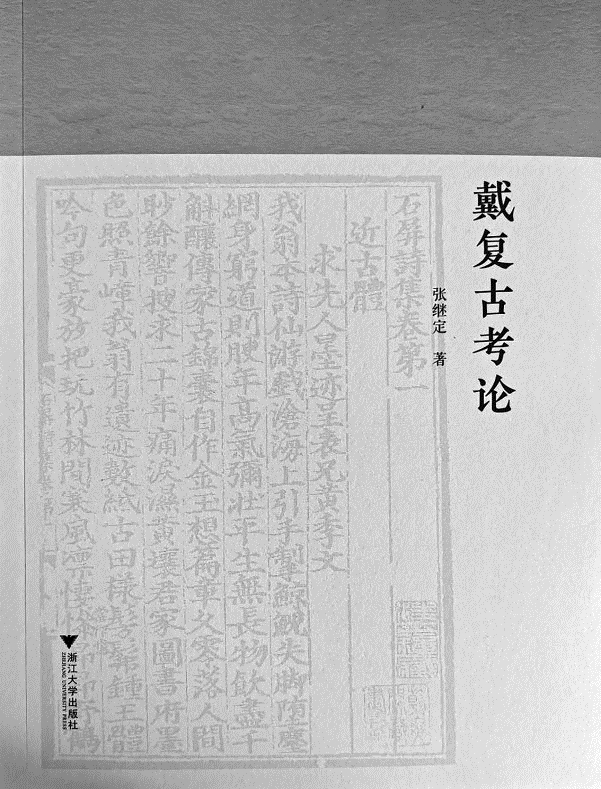
□ 张继定
《戴复古考论》是笔者三十多年来关于南宋江湖派著名爱国诗人戴复古研究的论文结集。由于其内容主要是戴氏身世经历及其作品诸方面的考证辨析,姑且以“戴复古考论”名之。
论及考论的写作,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徐复先生(1912—2006)曾有一名言:“考论之至者,语必摭实,义必综贯。唯其摭实,故语不蹈虚;唯其综贯,故义不偏至。”①说来惭愧,徐老先生关于考论的这一论述,我闻见已迟,更不曾认真践行过。
1958年8月,我从台州温岭中学毕业,随后就读于杭州大学中文系。1962年自杭大毕业后,分配至新组建的浙江师范学院(1985年改名为浙江师范大学)从教,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古典文献学包括考据学专业的学习和训练,也没有认真研读过南宋江湖爱国诗人、温岭乡贤戴复古的诗词作品。
笔者后来之所以参与戴复古及其作品的学习与研究,实有赖于台州温岭市的亲朋师友们的激励帮助,有赖于学界多位专家的指点、引领和提携。
由于戴复古是古代台州地区诗歌创作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而台州温岭又是戴复古的故乡,当地政府和许多学者都十分重视对这位乡贤的推介和研究。在温岭市政协副主席、文史专家陈诒先生的鼓励下,市报道组的吴茂云先生撰写了《戴复古家世考》,刊载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好评。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温岭市有关部门批准,温岭市戴复古研究会成立,创办内部交流会刊《石屏》,并经常开展戴氏作品的阅读研讨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国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刘扬忠、张宏生、胡可先等先生的积极支持,也激发了我学习研究和考证戴氏生平及作品的兴趣和责任感。
1992年至2005年期间,笔者先后在《石屏》内刊和省内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戴氏研究的文稿。只是囿于个人学识有限和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不足,这些稿子显得肤浅平庸而缺乏创见,加上自己治学粗疏,文中还出现诸多知识性差错。例如《关于弘治本〈石屏诗集〉及其点校本的几个问题》一文,把宋愿父说成“名自逊,号壶山”,实则这个说法是错的。据当代学者熊海英考证,宋愿父并非“名自逊,号壶山”,“愿父”乃宋氏六兄弟中的宋自逢、宋自迪其中一人之字。②更有甚者,拙文《戴复古佚诗辑录》中出现的差错更多,幸蒙北大王岚教授撰文予以纠正(详见王岚《〈诗渊〉所收戴复古集外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1期),才避免拙文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反思自己2005年前所撰戴氏研究文稿的问题,似可用两个字来概括:粗浅。粗者,粗疏也,包括文字差错和知识性失误;浅者,平庸也,卑之无甚高论。正打算退休后重新起步补习专业知识,加强考据方面的理论学习和写作训练,克服存在的问题,不料2006年突患一场大病,几乎一蹶不振。经过数年的治疗和休养,虽然身体有所恢复,但慢性病依然缠身,思维能力不断衰退,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断了关于戴复古及其作品有关问题的研究,每以无力接续原来的戴氏研究计划、提高考据写作的水平而自憾。
帮助我逐渐走出自卑困境、重拾考论写作信心的是学界多位专家师友。
2017年,温岭市为纪念戴复古诞辰850周年,联合全国宋代文学研究会共同召开了一次戴复古研讨会,国内有不少著名专家学者与会。他们精彩纷呈的报告和发言,给了我诸多有益的启发。庆幸的是,先前对拙文有过校正的《全宋诗》编委、北大中文系王岚教授,这次也应邀与会了。会议期间,诸位专家学者针对我请教的有关问题与我多次亲切交谈,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个人治学为文之不足和失误,也只能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去改进,不必过于自卑。他们的指引和鼓励,令我大受感动,从而也增强了我考论写作的勇气。拙文《钱锺书先生对戴复古〈世事〉创作的误解》就是在王岚教授及沈松勤教授的分别指点下撰写并改定的,最终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2期。
2019年10月,应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学研究中心的邀请,我参加该校承办的全国“四库学”研讨会,与会的北大吴国武教授和首都师大的一位教授,虽然与我素昧平生,却对我这个年高而学浅的后进生热心地出以援手,认真帮助我修改参会论文。特别是会议主持者、首都师大历史学院教授、四库学研究中心陈晓华主任,百忙之中还引导我扩大研究视野,把戴复古研究与四库学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让我找到了当下戴氏考论写作的一个新选题。经过一年多收集、校勘有关文献资料、起草文稿并反复修改的过程,我终于写出一篇题为《戴复古“江西重婚案”与四库馆臣求实精神》的长文。此文经陈晓华先生的审改与推荐,被首都图书馆编入《盛世文华四库纵谈》一书中,由学苑出版社于2021年11月出版。虽然该文的考辨与论证仍有某些不足,但对个人来说,毕竟是一个进步。
回顾上述写作的曲折经过,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如果没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诸多同事、师友以及校图书馆老师的多方支持与帮助,如果没有省内外学界(包括有关书刊出版单位)相关专家学者和编辑们的指导和审正,如果没有台州温岭亲友们的教导和鼓励,本书是很难得以编印出版的。
同时,这一回顾,也使笔者由浅入深地认识到本文开头所引徐复先生的名言对考论写作之重要意义。所谓“摭实”,就是摘取并依据事实真相加以说明,而不能凿空造假;所谓“综贯”,意谓总括贯通,强调的是综合、全面地分析理解事物或问题的意义,避免片面性。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人们在考据时应实事求是,从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探取事实真相,避免各种虚假伪饰信息的迷惑和蒙蔽,进而综合、总括性地贯通论述事物或问题,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
按照这一要求,我觉得从事文献考据时,以下几点是需要尽力注意的:
其一,要尽可能多地收集文献资料,认真校勘核实。倘若一看到以往未曾见过的新材料,只看前面部分,未及全篇就轻下结论,往往会误解该文献的原意。
其二,古代典籍包括各种史志和笔记,往往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相当多的方志或笔记,例如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和元末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于史实之中常夹杂着著者之臆想或未经核实的道听途说,可谓真伪杂陈。对此,需要多方考证,客观分析,辨其真伪。某些文献编著者把有关戴复古重婚的记载当成史实引用,进而对戴氏大加斥责鞭挞,恐怕是对《辍耕录·贤烈》这则笔记缺乏深入考证与客观分析所致。
其三,古今一些名家名著和影响较大的辞书或丛书,亦有少数舛误。特别是古今文献中人物的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等等,有时由于编著、抄写或制作者的笔误或记忆失误而难免发生差错。对此,我们既不能以微瑕而否定其全璧,也不能因是名家名著而讳言其讹误。
这里仅举一个与笔者有关的例子。
某知名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唐宋词汇评》,以其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编排新颖、富有特色而赢得广泛赞誉。然该书第四分册介绍戴复古的资料时,却有一行不实的介绍:“【年谱】张继定《戴复古年谱》(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笔者自知水平有限,至今不曾动过撰写戴氏年谱的念头。我曾为此事向出版社探询,才知此乃该章节撰稿人记忆失误所致。为避免盗名窃誉之嫌,笔者顺便在此予以更正说明。
收入本书的大多数文稿,曾先后始发于国内的多家学术期刊。鉴于各家期刊对稿件的规格体例要求不一,故这些文稿编入本书时,其原有的格式体例不得不按照本书的格式要求,予以相应的改变和调整,删去了各篇论稿题后之内容摘要和关键词等文字。至于正文,则基本保持始发稿的原貌,若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包括原稿存在的大的失误),则在文内或文后加按语予以说明;原稿中少数文字标点的错讹以及个别表达欠当之文句,收入本书时亦尽力作了相应的修改润色。只是,限于著者水平,书中肯定还有诸多不当之处,祈望方家和广大读者多予指正。
【注释】
①徐复:“序”,见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序”第1页。
②参见熊海英:《晚宋江湖诗人宋自逊家世生平与交游创作考论—兼及对南宋“江湖诗人”和“江湖体”的再认识》,《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99—109页。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