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今日诗歌的另一个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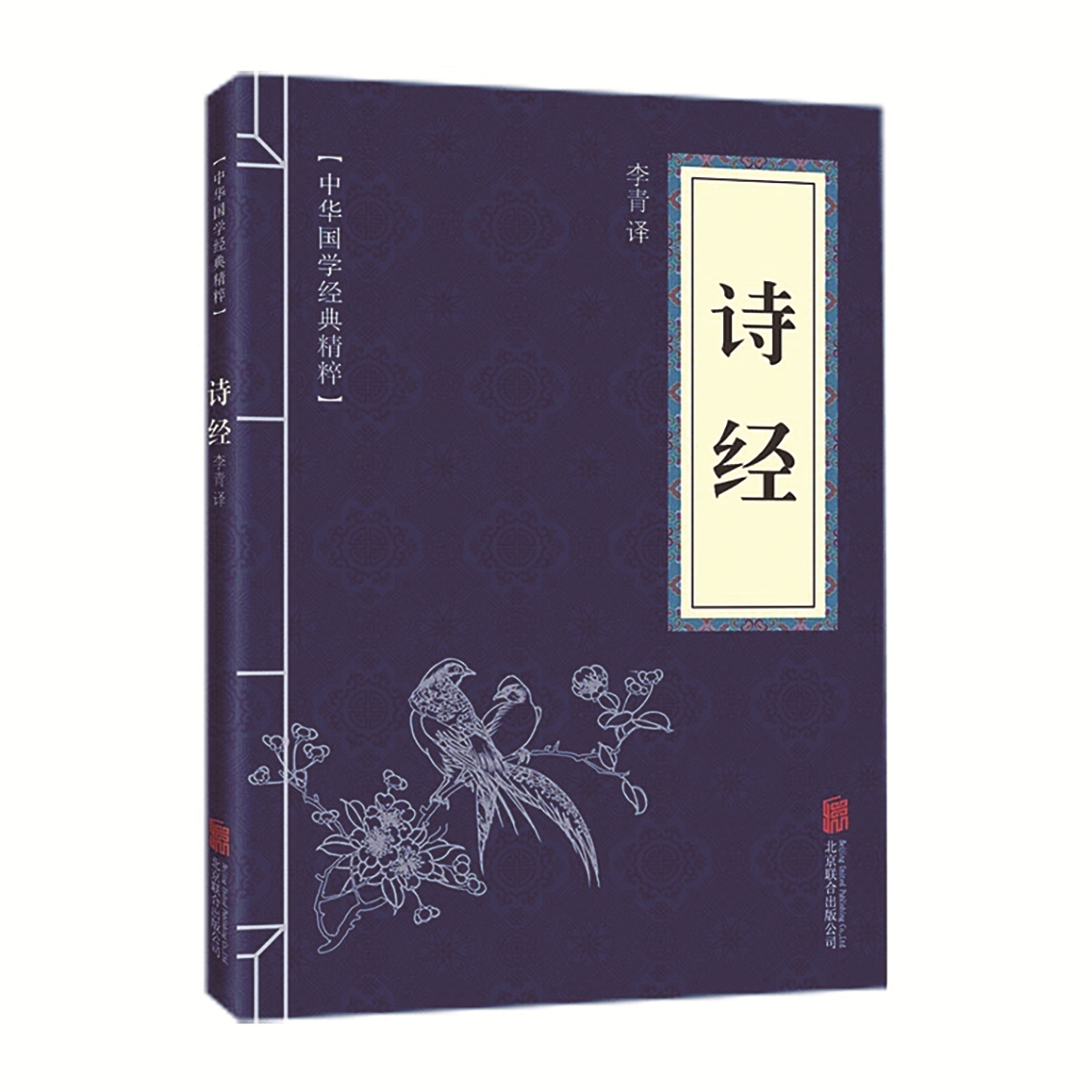
□ 邢海珍
在漫漫的历史长路上,《诗经》向我们走来,背负着两千五百多年的高龄,它用沧桑的眼睛看我们。一路经历了太多,有坎坷也有辉煌,两千多年诗歌发展的蓬勃之势证明了它的伟大。《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几乎所有用汉字写成的诗都直接或间接地承续它的基因。《诗经》的诗意描写,开启了感性状态表现人生景观和人性精神深度的先河,为人类的文学找到了一个出口,确定了一个基本形态,尤其为诗的形成标举了明晰的方向,为汉语的言说者拓清了一条诗学实践之路。
我们一直朝前走,诗有未来,那是诗前行的远方。而《诗经》是我们今日诗歌回头看的另一个远方,是诗歌历史回望的远方。它是民族文化的景深,是一种根基式的文学脉动,是底蕴和底气之所在。
作为汉语诗歌的源头,《诗经》至少在两个方面为后世诗歌注入了生命的活性因素,传递了健康发展的良性基因,这是诗歌发展最为重要的经验。
一、在具象性的抒情中构建了人生世界“现场”的景观
如果说文学的境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那首先是一个“人生世界”,人生的属性是文学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诗经》作为“诗”而打开文学的大门,它选择的是人生的向度,由“人”的生命活跃其间,人的情境、人的现场、人的由内到外的情感世界构成了一个活跃、完整的境界和景观。
《诗经》所表现的文学内容是诗的样板,为后世诗歌的发展敞开了一条宽阔的大道,这就是包括人情、人性在内的人生世界的大范畴。比如秦风《蒹葭》描写“蒹葭”清寒淡远的自然景观,引入了企盼“伊人”的情思,包含了情爱意蕴的人生“现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首苍茫辽远的诗,芦苇在远古开花,秋露霜风,水波荡漾,缥缈的境界中是思念的人,如梦似幻。远远近近,似有若无,以美好空灵的景致,衬托出内心的思念之情。主客观互融互渗,自然景象的描写中包含了诗人内心激荡的情感。
从《诗经》中的许多诗作看,抒情是诗的主要艺术表现方向,是作为抒情主体人的内心世界的呈现。但这些诗不是空泛地直陈内心的感受,而是借助于“物”,即写景、写人物的行为、写事物的形态状貌,从这一点看,《诗经》是重视“及物”的,后来所说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诗歌写作的艺术手段都与此有关。抒情的定位是开启先河之举,从《诗经》之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一直到今天,诗歌的观念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抒情作为立“诗”之本还是无法改变的。泛情、滥情、煽情当然不好,诗的抒情则不能不要。零读也好,冷抒情也好,其实还是抒情,只不过是方式有所不同,没有了抒情或是削弱了应有的情感因素,诗歌文体就会受到致命的伤害。
诗歌中的叙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是改变了叙事格局的“伪叙事”,在诗歌中可以看作是叙事性或叙事因素。叙事性、叙事性与抒情并不矛盾,或可作为抒情的基础性元素而存在。《东山》《采薇》等诗作都有较强的叙事性,但在整体的抒情格局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具象性内容,是抒情的依托。
诗的抒情是具象性的,而具象性不可能没有叙事性,要想构建人生的景观,叙事性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在诗歌发展史上,虽有独立的叙事诗作为文体形式出现,但也还是一种“抒情”的变革,抒情和叙事常常呈现出一种互融的状态。像后世出现的《孔雀东南飞》这一类诗歌,虽有较强的人物故事出现,但既是赋予了歌谣的体式,本身就是强化了感喟、叹惋的情感色彩,与一般的叙事不可同日而语。到了唐代的白居易有《长恨歌》《琵琶行》一类长调歌行,诗中也有相当的叙事因素,但与《孔雀东南飞》比起来却是叙事性有所减弱,抒情的力度明显加大,而其中的“叙事”具有人生景观的实在性,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物性基础,抒情仍占据主要的地位。就文体的特性来说,诗歌忌泥实而趋向于虚化,在实与虚的处理过程中是驾虚驭实,而不是避虚就实,抒情是大于叙事的,叙事是抒情所借助的因素。
《诗经》的出现,无论是形体状貌,还是在诗意表现的范畴,都有定位的意义。比如四言的格局,赋予了诗以节奏感,以外形促成跳跃的空间性可能。最为重要的是人生景观的确立,生活生存的现场,有足够的感性、具象的直觉性,造就了人情人性的“软”形态。追求生活的情境之美,尤其是人情人性之美,《诗经》可说是写作实践的源头。描述人的行为、动态的人生世界的景观,与那些叙事、论理的文体有了鲜明的形体和表述方式的不同,对于诗歌文体独立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象喻和思辨的深度打开了人性精神之门
在审美的创造中抵达人生和生命的本真,《诗经》具有自己从容而原始的深度,甚至它的简朴和本色中自带神性,为人类文化的起点由生存的根基指向了终极的目标。中国的文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不无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但又不是绝对地遵循着臆想的简单的进化过程,而是从开始的起点就确立一种生命精神本质和艺术自足的品位。就像松树从幼苗开始就是松树而不是蒿草一样,不因原始而使品质一定处于低级状态。
如果说《诗经》是起点,是人类文学的青春期,而它所提供的诗歌作品是单纯中蕴藏了丰富与深刻,而绝不是简单或简陋。它给后世留有的发展空间是幼苗长成大树的空间,而不会是老鼠进化为大象的过程。我们的诗从源头流出就是一条美质丰沛的先河,不乏象喻的鲜活感性的形象,不乏情境的内蕴,不乏诗之思的深度追求。《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就是充溢着人情人性之美的诗篇,写河边的自然环境,雎鸠鸟在鸣叫,有了人活动的场所。这是文学描写中的自然环境,但又不仅仅是自然环境,从上下文的联系中,还可以看出一种“隐喻”的内在因素。鸟儿鸣叫,不无求偶的可能,与下文所涉及的男女之情是比喻、象征性的内在意义的联结,环境、人物的描述本身即有很强的感染力。诗行是跳跃的,先写鸟后写人,二者之间是跳跃式的空白,看似没有联系,内在却隐含着映照、象喻的关系,是情感与美的具象性投射。
后来人们对于《诗经》的研究总结提出“赋比兴”的表现方式,其中比、兴成为诗歌最为本质性的艺术手法,使诗歌在艺术化、心灵化的阳光大道上健康发展。宋代诗论家李仲蒙认为“赋比兴”都是抒情的不同手段,“触物以起情为之兴,物动情者也”(引自宋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其特性在于物与情之间存在着一种松散联系的“隐”,其思辨的可能性使情感的表达进入了深度的新天地。
《诗经》走的是一条审美之路,是直接连结生活、生存的人生“现场”,使主体的情感寄托和抒写有了具象的载体,为后世的诗歌文体壮大铺设了基础性的坦途。在诗学实践中,情感抒写的基本形态是“情思”,但不是情与思的分离状态,而是不可分的融合。一旦有了明显的分离迹象,就可能出现“情”的浮泛或是“思”的抽象而使诗的象与境失衡,给诗的审美造成损害。
《诗经》的比兴手法是源头活水,对于诗的文体至关重要。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无意地忽略比兴之法,还是有意地淡化比兴之法,都可能造成诗歌艺术表现上的短板。新诗如果不在语言色彩、比喻象征以及技艺手法上做文章,只是一味地把散文分行,就会失去诗的文体特性而使诗意萎缩。旧体诗如果忽略了比兴等传统的诗化方式,而只是在格律上做文章,也会使诗失去血肉的活力和光彩。
在许多日常描写中,《诗经》常常表现出一种关乎终极的悠远之思,具有一定的哲学意识,这是诗在原初时代所表现出的深度追求迹象。比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是心思向远的典型例证,“伊人”作为一个意象出现在诗中可以指代、隐喻更为广泛的事物,而蒹葭白露的意境有着深切的内蕴。
生活和人生现实的具象性描述,是诗歌意境和意象感性品质的基础,而诗中的感叹式的歌谣,尤其是其中的音乐性,则深化了情境,有了“思”和思辨的可能,使诗的抒情可以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在单纯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复杂的因素。《诗经》中的生活场景的呈现以及景物描写中的悠远情怀,就是文学最初的人情人性基因,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为人生文学景观的早期出发点。
《诗经》所写的生活情境,多是写实性描写,是当时时代的反映,体现了诗歌所具有的拥抱现实的艺术特性,这是需要不同时代都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即使我们今天写旧体诗,也绝不是我们的情感和话语返回了古代,不是写古代人的诗。诗人们可以使用旧体,但又必须从既定的思维格局中走出来,从话语的固化套式中走出来。我们是现实时代中的人,不是古代的人,要写今天的诗,充分表达现实的、与我们现实人生命运息息相关的情境与情怀。《诗经》留下了远古的生活情境,我们读诗可以看到当时的时代影像,这是重要的诗学价值。我们今天写旧体诗,不能只是读一些古人的诗,不能还是延续他们的一些习惯性语词,走不出他们情感的思维模式,这关乎我们现实生活的情景和情感能否得到充分表达的问题。诗与现实脱节,本质上就是消解了我们作为诗人的价值,背离了《诗经》所传递的基本诗歌精神,对此我们应当深长思之。
(作者系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